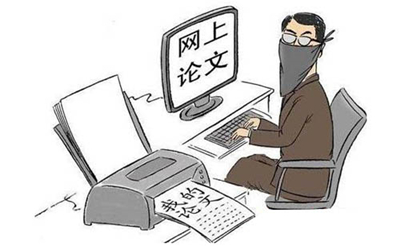

近日,因“伪造同行评审的痕迹”,英国某大型学术出版集团撤销了43篇论文,其中41篇是中国作者。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更大范围的“造假”正在污染学术出版圈。
据数据显示,我国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凤毛麟角。当下,大量学术期刊已经完全市场化。交钱就能发表论文的现实,已然造就了我国论文发表与职称评聘工作的“假大空”现象。竞争压力、急功近利、经济成本、监督机制、科学评价的施压等原因造成的学术不端和科研失范,极大地腐蚀了科技界的肌体,损害了科技工作者的声誉。如何清除这块肿瘤,恢复其本来应有的面目?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越来越猖獗的论文工厂。多位研究人员告诉《知识分子》,近年来论文工厂在国内越来越猖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的徐奇智表示,过去的学术会议上,就经常会遇到论文工厂的中介人员来发名片,现在这些中介更是“进化”到混入学术会议聚餐环节的餐桌上,装作和各位研究人员同属一个圈子,和大家互换微信。要到联系方式后,中介就会大量发广告。 “前几年还好,只是说他手上有什么期刊,大家可以找他代投。现在更离谱,直接把论文的题目都给出来了。比如现在有20个题目, 老师你只用把钱一付,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徐奇智说。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主任药师周小明提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一位医生曾经想要从中介那里购买论文,但交了定金之后反悔不买了。结果中介公司直接把催款的电话打到了医生的单位,表示“你们的人买了我们的论文,现在稿子已经投了,他的尾款还没交。” 徐奇智之前对中国因图像学术不端撤稿的论文作过分析,他发现中国图像学术不端从2013年开始大规模出现,而且两三年内迅速达到高峰,直到现在仍处在高峰期。而且图像学术不端撤稿数据的增长和论文工厂大规模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图像学术不端的一大问题是图片复制。徐奇智告诉《知识分子》,很多因为图片复制撤稿的论文,复制的都是同样的图像,尽管他们的作者之间都毫无联系,这暗示着背后很有可能存在有组织的造假。 “最合理的解释应该就是论文工厂。”徐奇智说。“个别作者有可能截别人的图片来用,但这么大范围的图片重复解释不通,不太可能这么多人都抄同样的图片来用。找他们买论文,他们可能就是一套图来回用,只是裁剪下或者调下亮度、对比度,局部涂改一下。” 《知识分子》曾在过去有关论文造假的报道中,介绍过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识别论文工厂的研究。论文工厂出产的论文从最早的每年几篇,逐年增多,到2014年已到每年百篇以上,2018年后更是到了每年千篇以上。SCI论文中,医院是发表论文工厂的论文重灾区,占67.5%。并且全球医院发表的SCI 论文中,产自工厂论文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医院[9]。 王景周表示,根据他的追踪,论文代投代写的问题从2010年以来就比较严重,中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论文工厂的造假买卖也在那时开始出现。2012年后,因为一些期刊的审稿平台上线,投稿信息注册信息可以回溯,这些学术不端由此被发现,引起了全球的重视。 国际上的大规模撤稿事件往往会引起国内的关注,但徐奇智认为,相比信息公开的国际期刊,中文期刊可能潜藏了更多问题,论文工厂和中介也有更多运作的空间。一些论文中介会声称中文期刊编辑有着联系,连论文题目也已经定好,只需要付钱就可以发论文。如果论文中介不是在诈骗,可能就是期刊编辑参与了灰色产业。 “如果真要查这些论文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撤稿的比例可能不见得会低于国外的期刊。”徐奇智说。撰文丨张天祁
 (0)
(0)
论文已经成为部分科教管理者手中的权力与“武器”。论文,特别是SCI论文,甚至已被权力化了。 部分领导者,他们是论文挂帅的倡导者与实施者,对西方模式与标准的崇拜,成为他们固化的习惯。 他们竭力宣传SCI论文对科学家及其成果科学性的重要意义,作出大量的检索统计,出版大量介绍资助对象的人才与论文、影响因子等指标的报告、宣传物。 对其资助的人才与SCI成果以及外国人的好评进行广泛赞扬;通过以项目、经费、荣誉为手段,对广大申请经费学者加以鼓励,对部分学者及成果进行贬低乃至封杀。 有些管理者,对学术界的不同声音满不在乎。“学术自由”“发挥科学家积极性”等很可能成为他们坚持这样做的理由,也是他们应对中央高层的“挡箭牌”。(作者:陆大道,中国科学院院士,经济地理学家)
 (0)
(0)
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和专著。目前,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讲究的是质量,像德国的教授,一年发一篇论文就可以了。
 (1)
(1)

王健:2020年全球撤稿英文论文1932篇,来自中国819篇。其中,639篇以上撤稿通知提示涉嫌学术不端。撤稿数量前三位为吉林大学、青岛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撤稿共涉及436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包括杰青)和79个科技部重大重点项目。超过377篇论文的撤稿通知提示图像涉嫌篡改或造假。“图片误用”问题不解决,还会有更多人前仆后继,继续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0)
(0)   1 1   共6条信息
共6条信息 |